樟树下|平凡中的微光

流动菜摊
在我的老家西窑村,时光比别处好似要慢一些。都早上六点多了,整个村庄还在沉睡之中,田野、小路、远山,都十分安静,连天上的云也静止不动。直到一阵“嘀嘀嘀”的喇叭声从远处传来,才把村庄从睡梦中叫醒。这是邻村的李哥开着车进村来卖菜了。“排骨,牛肉,卤肉……”随着高音喇叭里叫卖声声,退休回乡的母亲和父亲也起来了。“哟,我的猪脚到了。”父亲一边说一边“吱呀”一声打开门。很快,邻居家的门也都“吱呀吱呀”地响起来,一些细细碎碎的脚步声和说话声陆续朝着菜摊车飘去。
李哥的车停在村里老马家的门前。车厢里放了大大小小的箱子,分门别类地装了牛肉、猪肉、火腿、卤鸡爪、盐水鸭等肉菜,水产品则有鱼、虾、螺蛳、泥鳅等。看准了村民家种的蔬菜品种有限,李哥会根据季节来打时间差——冬天卖大棚种植的辣椒、茄子、西红柿,夏天就卖西芹、蘑菇、藜蒿等,绝不会与村民自种的菜“狭路相逢”,他要让乡亲们尝到自家菜地里没有的蔬菜。李哥的菜都很新鲜,蔬菜的颜色碧绿鲜亮,水箱里的鱼不停地游动着,扑打出水花。菜的数量虽不多,但品种齐全,凡是菜场里有的,在这小小的车摊上几乎都能找到。李哥的菜摊车就像一个微型菜场,会四处流动,流到偏远的小村庄,流到各家各户的门前。
来买菜的村民越来越多。菊花嫂子买了肉、鱼和螺蛳,福兰婶子买了孙子爱吃的卤菜,琳琳买了玉米准备炖排骨,父亲除了提前预订的猪脚,还买了香肠和小米椒……黄叔家乔迁新居要摆酒席,他写了十桌的菜单交给李哥,李哥爽快地说:“全部按批发价给你,明天送来!”李哥的批量送菜服务又省钱又方便,很受村民的欢迎。
也有不买菜的人,端着茶杯来凑热闹。李哥一边有条不紊地称重、装袋、算价钱,一边和大伙儿拉家常。他性子温和,微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,说得最多的是:“放心,乡里乡亲的,不会算你贵。”确实,李哥菜摊的价格一直比较公道,有的甚至比镇上菜场的更便宜。遇到村民讲价,李哥还会大气地甩甩手,“好好好,零头抹掉吧。”然后少收个一毛两毛的,或者给顾客多放一片豆腐干、几个小米椒。买菜的人便心满意足又略带感激地拿出手机,扫二维码付款。
绿色的二维码牌子就挂在车厢的栏杆上,牌子在空中飘荡,响亮动听的“微信收款某某元”的声音在村子里飘起,李哥听着,脸上便有藏不住的笑意。
是啊,能不开心吗,之前他一直在外打工,四处漂泊,后来发现很多村庄离镇子远,留守的村民买肉菜不方便,李哥便开始做上了流动菜摊的生意。每天一早就去批发市场接菜,再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去卖。转完固定的路线,刚好就是一天。流动菜摊,不仅解决了村民买肉菜的问题,让村民的餐桌丰富起来,还让李哥的生活也稳定了下来。
没多久,一辆卖水果的车子也进村了。于是大家又围到了水果车旁挑挑拣拣,西瓜、苹果、梨子、火龙果……水果们四散着跟着村民回了家。李哥这边的生意差不多也结束了,只见他麻利地收拾好大小菜箱,发动车子绕到了大马路上。
“新鲜的排骨、牛肉、鱼虾……”高音喇叭里李哥的叫卖声时高时低,随着风向下一个村庄奔去。
(伍晓芳)
墙角的薄荷

小暑的天往下坠,蝉叫得人耳朵里发木。柳树叶子打了卷,边沿枯黄,渴得厉害。风也是热的,挨着皮肤滑过去,留下一层黏糊糊的汗。这日子,闷罐子似的。
墙角砖缝里,孤零零杵着几棵薄荷。细秆子,薄叶子,灰绿的,混在野草堆里,没人会多看一眼。它就长在这些地方,土薄,日头也晒不着,是连光都懒得落脚的去处。
小暑的雨没个招呼,天猛地裂开口子,雨水卷着地上的热气,鞭子一样抽下来。雨停了,我踩着烂泥去看墙根的葱,脚却被那几棵薄荷勾住了:它们全趴在了泥汤里,秆子折了,叶子破了,污泥糊了一身,脸朝下栽进泥里,像是被谁的大脚板碾过。
可就在这烂泥滩里,一股子清新气息猛地蹿过来。那味儿冲鼻,带着股蛮劲,生生顶开了四周厚墩墩的热气。它往鼻子里钻,往脑腔子里沉,叫人一个激灵——是薄荷的骨头断了,汁子淌了,它藏着的那点凉气,才不管不顾地全炸了出来。越是揉烂了,踩扁了,那味儿倒越冲,越透亮,像是从泥里挣出来的一声闷喊。
过了两三天,大清早我又晃到墙根。断了的薄荷老秆子边上,竟一窝一窝拱出了新芽。露水珠子挂在嫩叶尖上,太阳一照,亮得晃人眼。那绿气儿,比下雨前还足,还精神。这点不起眼的活物,在烫人的节气里,硬是从断口上又挣出了命。
我蹲下去,手指头碰了碰那些带伤的新叶子。一股凉气顺着指尖爬上来,那凉里头,裹着股摔打不烂的韧劲儿。这哪是植物的气味啊?分明是活物在泥里滚过,摔打出来的骨气,叫人想起后街种菜的老杨婆,日头像下了火,她弯着腰在地里薅草,汗珠子砸进土里“噗噗”响;又想起巷口补鞋的老李头,守着他那巴掌大的摊子,破收音机传出咿咿呀呀的唱戏声,满街的车喇叭也盖不住。他手里的那根线,一下一下,捻得又细又匀——他们,不就是这人世蒸锅里,另一把活着的薄荷?世上的风雨踩着脊梁过,日子里的砂石磨着骨头走,可骨子里那点透亮的东西,反倒越磨越硬实,越捂越悠长。
后半晌,蝉吵得人脑仁疼。我蹲在墙根,盯着这点绿。它不是什么金贵东西,就爱长在这犄角旮旯,悄没声息地活着。可偏偏是这热浪最凶的时候,它用自己的身子骨,熬出了最顶事的凉气。那味儿在闷罐子里左冲右撞,是活着的动静:就算被踩进泥里,也得用骨头缝里攒下的那点凉,顶开压下来的热。在不起眼的地方,也能透出自己的一股清气。
我掐下片带伤的叶子,指头肚一捻,凉丝丝的汁水就渗出来。它被揉烂了,倒把攒下的那点凉气,一股脑儿抖搂了出来。它像是认准了死理:活着,不是躲开这世上的烫,是用骨子里的那点凉,去扛,去顶,去挣个明白——它的香气,终究会悄悄爬上过路人的裤脚,透着一股无声无息的硬气。
隔壁小孙子让暑气拿住了,蔫蔫地躺着。我掐了几片嫩薄荷叶,在手心里揉出汁子,抹在他滚烫的太阳穴和额角。清气在闷热的屋里散开,孩子紧锁的眉头,也慢慢松开了。他奶奶瞧见了,没吱声,转身到院里,也掐了一小把薄荷叶,丢进灶上煮着的凉茶壶里。茶叶沫子沉浮着,薄荷叶子也跟着打转。她说,伏天燥,喝点这个,心里头利索。
墙缝里的这点凉气,就这样,渗进了人的日子里。
(魏咏柏)
梅桂的生日
村里老人有句古话“世上只有手摸脚,没有脚摸手”,这是用来形容父母对子女的爱。
母亲有五个姐姐,没有兄弟。从老大开始,名字分别叫秀花、水花、春花、冬花、茶花,轮到我母亲,谁也没想到,外公来了个“急拐弯”,给母亲起了“梅桂”这个名。
“梅桂”不带“花”字,却还是透着芬芳的花。
母亲一直生活在老家。两年前,我女儿出生,两年后我从市里调到了近两百公里远的县城上班,为了照顾我们,母亲一起到了县城。
我选择了租房。房东人好,床垫换新、水管快修、儿童防护等做得十分贴心,住得还算舒心。美中不足的是,进门的智能锁还不够“智能”,母亲常年劳作,拇指指纹早已磨损,锁时常感应不上,以至于老出现开不了锁、进不了门的尬事。
又一次,母亲指纹识别错误次数超限进不了门,遂联系房东。
“房东人好,喊来了师傅,开了门,把系统清了,换成了密码开锁。”母亲告诉我,“密码是731205。”
怕忘记,这串数字就被我记在手机里。
接下来的日子,母亲带娃我上班,我们进出家门的时间不同,每每开门,我都要拿出手机确认那串数字。
暑假,母亲回老家了,当老师的妻子来县城接过带娃的重任,我把密码发给了她。
妻子比我细心。我下班回家,她悄悄问:“门锁密码好像是妈妈的生日?”
“731205不就是1973年12月5日吗?”听她这么一说,我才反应过来,那串在手指里跳动无数次的数字还真是母亲的生日。
于是每进一次门,每输一回密码,我就多一次机会记住母亲的生日。
九月,妻子开学回市里了,母亲又到县城接过带娃的接力棒。日子平淡,梅桂在娃的“咿咿呀呀”声中过得热闹又安静。
在重复的日子里,门锁密码被我记得牢牢的。
十二月五日到了。那天,我悄悄地买了一束玫瑰花,献给梅桂。看到散着香气的玫瑰,梅桂那张平日里隐在儿女孙辈后面的脸,明亮生动,笑成了一朵花。
(江日航)
文刀刘警官
小刘警官到派出所报到时,是有些不愿意的。学刑事专业的他,想着毕业后能像电影里的刑警,惊心动魄现场追凶。万万没想到,竟然被分到了派出所,成了一名与大爷大妈打交道的片区民警。
更让他猝不及防的是,刚到派出所,接到的第一个任务竟然是帮李大爷找走丢的小狗。李大爷是独居老人,为了排遣寂寞,养了一条叫“小小”的田园犬。那天在小区里,小狗挣脱牵绳走丢了,大爷急得不行。小刘警官接到指令后迅速出警,花了一个多小时,在小区偏僻的游泳池边找到了“小小”。李大爷激动地握住小刘警官的手摇个不停:“警官,谢谢你了,你叫啥名字?”小刘一边抹着汗,一边笑着说:“大爷,我姓刘,文刀刘,小刘警官。”李大爷耳背,没听全,直朝他竖大拇指:“文刀刘警官,你真厉害。”小刘警官想纠正一下,但听说李大爷耳背,又担心说话声音大了让李大爷误会,干脆默认了。从此,小刘警官成了片区里的“文刀刘”警官。
基层派出所,哪有那么多的惊天大案呀,整天就是些鸡毛蒜皮的“案子”。今天王大妈的钥匙丢家里进不了门,明天曹叔家的车位被人占了闹纠纷,他都得去处理,整天忙得脚不沾地。
去年年初,张大婶加了一个微信团购群,一开始群主在群里发红包。时间长了,群主说这红包的费用其实都是他炒股挣来的。看着群主每天进账几百上千的,张大婶心动了,准备到银行转账给群主让其代炒股。文刀刘警官闻讯,及时赶到银行制止,并对张大婶进行了反诈宣传。当意识到差点受骗的张大婶颤抖地握着他的手,连声说着“谢谢”时,文刀刘警官算是体会到了社区民警的分量。
日子在调解纠纷、寻物寻人中悄然过去,文刀刘警官渐渐成了片区的“百事通”。谁家孩子放学晚归,哪个独居老人需要重点照顾,他的工作日志里记满了比案件卷宗更琐碎的烟火。直到去年夏天,所里值班电话响起:“一网上逃犯现身于你辖区,请派出所配合抓捕!”
一听说抓逃犯,文刀刘警官兴奋地跳了起来。抓捕行动特别紧张,在一个死胡同里,熟悉地形的文刀刘和逃犯碰了个面对面。他盯着逃犯,步步紧逼,逃犯见无路可逃,从腰间拔出一把雪亮的匕首,朝他冲了过来。文刀刘身子一闪、脚一踢,一记漂亮的左勾拳,再用胳膊肘一顶,反手将逃犯压在了身下,随着“咔嗒”一声,被铐上的逃犯顿时泄了气。
文刀刘警官的事迹很快在社区传开了。张大婶听说他没有对象,热心地要把在大学当老师的侄女介绍给他;王大妈热情地煮好了饺子,用保温盒装了送到派出所,非要他尝尝。王大妈上小学的孙子还专门画了一张奖状送给他,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:“送给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文刀刘警官。”文刀刘把这张特殊的奖状贴在了自己的工位上,让同事们眼热不已。
“扫楼”是片区民警的日常。文刀刘警官的警民联系卡贴在社区里,不知被哪个调皮蛋在上面画了一朵小红花,胖胖的像孩子的笑脸……文刀刘警官看到也笑了,他觉得,这片社区里的家长里短,还真就是他工作中的“大案要案”呢。
(肖日东)
九分钟的爱
她是我的同事,说话大大咧咧,做事风风火火。笑起来,脸颊上的几颗雀斑也跟着跳舞。
我们会彼此聊家庭、聊孩子。她父亲是半年前过世的,我怕她伤心,有意避开这话题,可聊着聊着,还是绕不开。
她父亲是脑溢血走的,才六十四岁,脑主干出血,请了高明的医生,也无力回天。
她和爱人出差多,女儿才上五年级,父母退休后,成了她坚实的“靠山”。虽然她在省城买了房,可父母住不惯,不过,为了照顾外孙女,两位老人还是随叫随到。
父亲出事在一个大热天,她接到母亲的电话,说父亲晕倒了。惊恐之中,母亲连拨了六个急救电话,不是按错了键,就是说错了家庭住址。等她匆忙赶到时,父亲已经躺在医院里,上了呼吸机。
父亲一直没有醒过来。她和母亲商量,租了一个带呼吸机的救护车,把父亲转回老家的医院,父亲一直说落叶归根,作为女儿,她觉得这是给父亲尽的最后一份心意。
下了救护车上的呼吸机,又上了当地医院的呼吸机,一上一下中,父亲还是走了。
她深深地自责和愧疚。如果父亲一直在老家,是不是会悠闲地在水塘边钓鱼,和老哥们打牌、喝茶、聊天,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意外,还能再活十年、二十年。
平日里,母亲小病不断,一生病就哼呀嘿呀,父亲却从不这样。她曾经以为,以父母的身体状况,有可能先走的是母亲。
她的心在流泪,或许父亲身体早就不舒服了,只是他不说,硬挺着。
这一次,父亲独自远行,目的地是一个叫天堂的地方。那个地方,没有返程票。
阳光下牵着小手的大手、生病时背着她的肩膀,都抽离了。父亲回家时习惯坐的沙发拐角,那凹陷的位置,她一直舍不得抻平。她觉得,那里还有父亲的余温。
母亲用的手机是她淘汰下来的一个智能机。父亲走后坏了一次,她拿去修的时候发现了母亲一次误按留下的一段录音:
“玲玲最喜欢吃你做的酒糟鱼,玻璃瓶洗好了,等会我就装满。”
“那个竹凉席、大蒲扇也带上,孩子买房还按揭呐,手头紧,多带一样是一样。”
“玲玲上次给我买的皮鞋也带上,皮鞋底子很软,肯定花了不少钱,带给咱女婿穿,我一个退休老头,穿布鞋、运动鞋就行了。”
“你就不怕女儿生气?人家费心给你买的。”
“没事,我就说穿上不合脚,大了,走路呱唧呱唧的。”
“傻老头,脑子还灵光哩,一下子就把这双老脚缩小了两个码,哈哈哈!”
…………
录音有九分钟,是父母从老家来帮她带娃前头一天的对话。每一次来,他们都大包小包的。
她说,很感谢母亲这次无意的录音,得以让九分钟的爱永久保存。这些话,是她最爱听的声音。
(张昱煜)
撒把少年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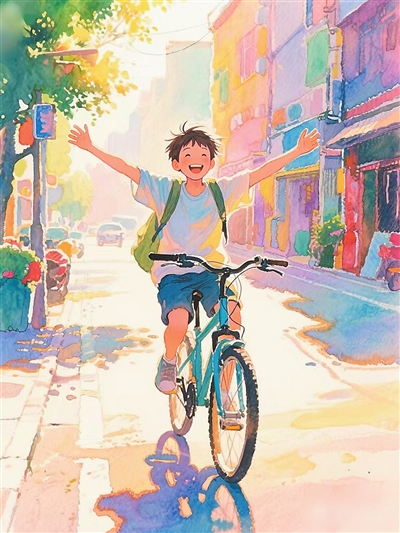
儿子今年初三,学习很忙,成绩一般。我和他妈很焦虑,总感觉他还不够努力,疲疲沓沓,“内驱力不足”。
报了辅导班,也不抵触。按时到,按时回,总感觉效果一般。
找一对一辅导,过了段时间,感觉不见成效,不了了之。
早上六点四十上学,晚上八点五分到家。吃饭,洗澡,九点左右坐在书桌前,十一点半之前上床。
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
“昨晚可能偷玩手机了,平时他不起夜,昨天晚上起来了两次,还把卧室门从里边锁上了。”我对他妈说。
“他也没手机啊,都藏起来了!”他妈说。
“不一定,可能借同学的呢!”我说。
旁敲侧击,突击检查,没有结果。
儿子喜欢历史。做题的时候,偶尔会抬起头来,给我讲晚清,讲二战,讲俄乌战争。
“这玩意儿考吗?”我问。
他继续低头做题。
初三几次模拟考,成绩都一般。但最近一次比上次进步了八十名,他回家炫耀自己的奖状。
“这成绩能上高中了吗?”我问。
“减肥啊,看你那肚子!”他妈妈在边上说。
教英语的同事在家给娃加“小灶”,他妈妈安排他参加。
我和他妈从同事家出来,让儿子从家往同事家去。
远远看到一个背双肩包的少年,骑着自行车从对面的马路驶过。刚过正午,路人很少。少年双手插兜,目视前方。大撒把,不很快,挺松弛。
我和他妈在马路这边,互相看了一眼。
儿子没有看到我们,继续前行。没多久,弯腰扶上车把,转个弯,看不到了。
“这孩子……”他妈说。
“如果没有中考压力,这孩子还挺开心的。”我说。
傍晚,他推门进家。
“骑自行车不能大撒把,得注意安全!”
我和他妈,几乎异口同声地说。
(刘胜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