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 者 这里有一份快乐的开学季书单,送给童年里追风的你们。愿你们的童年,浪漫且悠长,拥抱多向度的童心,沐浴自由和艺术的光芒。 国宝是可以属于儿童的 □ 郁 蓉 2020年的春天,我家两个小一点儿的孩子都宅在家上网课,上大学的女儿毛虫也回家了。家庭生活模式突然又切换回了孩子们的童年时代。一家人时时刻刻地团在一起,欢笑吵闹,柴米油盐,酸甜苦辣。 毛虫对中国文化极感兴趣,自学汉字,自制中国小吃,每日还临摹《芥子园》画谱。有一天,她看到chinoiserie风格(一种东西方传统文化创新融合后的艺术风格,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,是西方人想象出来的中国风情——奇异、神秘、和乐、理想又现实)的墙纸设计,就心血来潮地建议,在家中客厅画一幅这种风格的场景图,给我们的居家环境营造一种复古的风味。她的这个灵感一下打开了我储藏多年的欲望,我赶紧拿出我的宝贝:花枝俏线笔、小白云羊毫毛笔、一得阁墨汁,还有石青、石绿、藤黄、赭石颜料……说干就干!我们查阅了很多的资料,发现17世纪时期的chinoiserie风尚主题很明确,花鸟草虫、亭台楼阁、稻田耕牛、轻舟渔翁比比皆是。同时期,西方也开始广泛地接触中国的茶艺、丝绸、瓷器等经典传统艺术。我和毛虫构思了我们中国风壁画的墙面,从社戏到茶庄,从家居到织坊,用绚丽淡雅的色调还原出了一幅明清时期的江南风俗景象。 就在这时,戴芸发来了《你看见喜鹊了吗?》的文稿,让我心生灵动。故事里聚焦了几乎所有我感兴趣的中国元素!故事背景是国宝级古画《清明上河图》,这是一幅集市井、村野、人物、建筑、山水于大成,并且包容儒释道三家精神的风俗画卷,而最让我陶醉的是戴芸创作的贯穿整个故事的线索——那只带着五彩光芒、象征幸福的喜鹊。 在学习完编辑团队寄来的参考书籍《大宋衣冠》《大宋楼台》《风雅宋》《我们为什么爱宋朝》等后,我开始仔仔细细地阅读《清明上河图》。为什么说是阅读《清明上河图》呢?因为阅读是一种可以去咬文嚼字的看书方式,阅读一幅画则是一种步步可以观察、捕捉要素的看画方式。从《清明上河图》里800多个人物,到牛、马、驴等交通工具,到密集热闹、人来人往的虹桥,再到去城内赵太丞家就医的母婴,一幅幅社会生活的景象,都可以在阅读过程中栩栩如生、滴水不漏地展现。我需要这种方式彻底地和《清明上河图》做一次亲密无间的沟通交流。 戴芸从《清明上河图》中选取了15个景点,让原作画家张择端化身少年端儿,在画里从头到尾鲜活地逛了一遍。在途中,端儿每一次与画中人物的互动都很巧妙、生动、随性,处处隐藏着我们凡人的小幸福。比如端儿开头隐隐约约见到喜鹊,夫人送他柳枝,见证虹桥主仆相会,与乞丐分享一个烧饼,受到僧人点悟从而开始学习画画。这是戴芸杜撰的一个故事,放在《清明上河图》里却妥帖自然。 如何化被动为主动,这是我多年创作经历里最喜欢做的一件事。因为是根据古画延伸出一本全新的书,很大程度上是受原画限制的。这件事难呀,要抓耳挠腮地想。我想到了手风琴折页式一书二用的方案,利用传统古画横轴从右到左打开的方式,还原传统古装书籍从左向右翻的阅读形式。正面是戴芸融入现代理念的故事,反面是《清明上河图》本身。有了这条设计主线,如何去植入各类有趣生动的细节又是一个难题,而我就是冲着难题来的!我不断地阅读戴芸的故事和《清明上河图》,陶醉地围绕着那只带着五彩光芒的喜鹊,前后左右徘徊。喜鹊是在天空中飞翔的,端儿是在地面上走动的,端儿找喜鹊,怎么找呢?喜鹊会不会也在找端儿呢?如果我是小读者,我想在书里看到什么呢?这样反复斟酌后,答案便浮出水面了。正面,让端儿在画里从头到尾地找喜鹊;反面,让喜鹊在画里从头到尾地找端儿。最后的目标是,让读者跟着书里的两个主角,玩两场活灵活现地穿越北宋的游戏。 具体的创作是最愉悦的。首先是人物的设定,我的职业给予了我无止境的创作空间。我可以随性地造一个人儿:给这个人儿穿上衣服,衣服用什么颜色,红色还是黄色?这个人儿年龄几何,应该梳什么发型?这个人儿的裤子是单色的还是有花纹的?这一切都是由我去组合,这是多么让我沾沾自喜的一个过程。我参阅大量历史资料,研究了北宋时期男孩子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型,不同季节的服饰,终于,端儿在我的纸面上跳跃出来了。比如,我给端儿设计了一条红黄相间、菱形图案的裤子,红和黄是我们的传统色,而图案则是受北宋苏汉臣名画《杂技戏孩图》中左一孩童菱形纹样裤子的启发。人物敲定了,接下去是内页的风格:正面采用的是我擅长的剪纸和铅笔、彩铅相结合的手法,用《清明上河图》原画里的情节做背景,前景则把与端儿发生互动的人物和事物扩大展示,并且把这些人物的脸和端儿的脸都显示成白色。色彩的运用受chinoiserie风格的启发,清新、亮丽、雅致。穿红黄裤子的端儿与嫩绿粉红的街景遥相呼应。反面端儿和陪伴他的小狗,则参考了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创作方式,我按其人物的尺寸比例,找到有趣的景点,悄悄地把他们藏进去,让他们和原画里的人物有个互动,并且可以充当导游,带读者汴京一日游。比如,端儿和小狗在小舢板上捕虾米、喂鸭,在吊脚楼下看蛇,一起爬城楼…… 封面设计往往是最难的,这本更是如此。因为这是一本静中有动、动中有静的图画书,也是一个虚中有实、实中有虚的故事。我想到封面要和内文的故事有时间上的接续,并且能呈现出内文的绘画风格。于是,我是这样设计封面、封底的:喜鹊在封面上高高眺望着《清明上河图》开篇中的郊外送炭驴队,故事由此展开。可是整本书中,喜鹊根本没有出现,出现的只是被它的五彩光芒扫过而苏醒过来的古画里的人们。人们都在张望,目光和手指追寻着喜鹊远去的方向。一直到最后端儿开始学习画画,散发着五彩光芒的喜鹊才跃然纸上。随着画面的推动,五彩的光芒又汇聚到了封底的喜鹊尾巴上。整本书前前后后就是一个循环,无论怎样翻书,读者都会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。 现代的阅读形式是横排式的,小读者们通常接触的、适应的都是横排阅读,为了尊重孩子们的阅读习惯,我们首先选择横排。当我们把内文全部横排完后,问题出现了。因为画面视觉上的呈现形式是完全遵循《清明上河图》而设计的从右到左看的顺序,而横排的文字每段都是从左到右的顺序,几页读下来,我自己也搞得糊里糊涂了,好像两只眼睛在打架。从设计的角度看,横排也似乎有些不协调。于是我们尝试了竖排的方式,结果出人意料,效果非常和谐。我就想,这本书是根据《清明上河图》改编的,何不利用这个机会,让现代的小读者们深入体会一下我们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书画意趣? 你有没有发现:这本书的正反双面设计可以对比着看?反面中,端儿和小狗的行走路线围绕着很多景点。于是,编辑想出了几个游戏的点子,我们一拍即合,很快设计出了玩法小手册。希望读者们在阅读此书时,能与传统文化和艺术产生有趣的互动。 国宝并不是高高在上的,也可以是属于儿童的。如何让小读者代入到《清明上河图》中?我记得,我家的孩子们小时候很喜欢看捉迷藏绘本——《威利在哪里?》(Where's Wally?)。主角威利被藏在不同场景的人海中,读者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能发现他。孩子们往往被好奇心和好强心理驱使,会趴在地上花很多时间去找威利。所以我就想到了在反面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里藏入端儿和小狗,目的是引导读者从头到尾把《清明上河图》看一遍,找出所有的端儿和小狗,不知不觉中就能学到北宋时期的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。用玩的方式让孩子们爱上国宝《清明上河图》,这是我的“小心机”。 回到故事的核心主题——幸福。现代生活中拥有丰富的物质条件,可是这样的拥有并没有让我们更幸福快乐,真正的幸福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里。戴芸很好地利用了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市井生活,启发我们去发现和抓取身边的小幸福,用生活细节点亮我们的心。这也是我想通过鲜活的画面,传递给读者的。 公牛不都想 成为斗牛 □ 王园园 有人身处人群依然孤独,有人独自一人却灿烂如花。幸福可以是成为那登高之人,一览众山小,也可以是三两好友于微风和煦中静坐。不论何种幸福,最重要的是那个追求幸福的自己。人生没有既定的轨道,恰如《爱花的牛》告诉我们的,人生不过是一张拼图,我们总在前进中找寻自我的碎片,不断重建自己。 在《爱花的牛》中,我们的主角费南迪,作为一头越来越强壮的公牛,只喜欢花,喜欢“静静地坐在栎树下,闻闻花香”。而其他的公牛呢?“成天打架,用角去刺对方。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参加马德里的斗牛大赛。”爱花的费迪南,却因为大黄蜂的出现,意外地成了最凶猛的公牛,去参加马德里大赛。但费迪南没有被欢呼声裹挟,没有理会斗牛士的刺激,他只是看着“女士头上那些漂亮的花”“静静地坐下来,闻着花香”“人们只好把费迪南送回家”。回家后的费迪南,“依然坐在他心爱的栎树下,静静地闻着花香”“过得很幸福”。 费迪南是一头勇敢的牛,勇敢地让自己成为那特立独行的牛,不被定义,坚持爱花。不同于其他的公牛,他强壮的外表下,有一颗柔软的心,喜欢静坐和花香,不喜欢战斗。勇敢不是冒险,不是轰轰烈烈,不是打架,而如罗翔所言“是一种坚持”,是一种温柔的反抗。费迪南坚持着自己的热爱,尽管它不能带来荣誉,却能带来内心的富足与慰藉。费迪南“有幸”成了最凶猛的公牛,但他依然选择自己的热爱,没有理会标签、定义,将看起来无聊、不合群、孤独的生活,过成了浪漫且悠长的幸福生活。 圣·埃克苏佩里说:“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。”绘本不仅是为孩子准备的,也是给大人看的。费迪南勇敢活成自己,而长大的我们,却深陷定义、标签、人潮,失去了表达自我的能力,回头看看来时的路,那个更纯粹的自己是否依然可以被寻回、被拥抱、被偏爱?绘本用简练的文字展示生命和生存,用精准的画面表达喜悦和感动,这是来自心灵的力量,它为孩子感性书写,又为大人寻找失落的美好。 “不被定义”,不是叛逆,不是标新立异,是勇敢,是坚持。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,往往被定义,但那些与众不同,那些定义的反面,才是最动人和最真实的。孩子不需要成为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公牛也不都想成为斗牛。 爱的历险记 □ 吴镇宇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关于爱的定义。奥尔罕·帕穆克认为,爱是想要听到你的消息;到卡佛这里,爱似乎变成了关于彼此的回忆;在木心眼中,爱又摇身一变,成了那句“多给我读诗好吗”……爱是这样奇妙而又吸引人的情感。我们总想极力去追寻爱的定义,却总是捕捉到它的剪影,当我们回归童心,以最纯真的眼光追寻爱时,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它呢? 《活了一百万次的猫》给出了答案,这似乎是一本写给孩子的书,却回答了普通人爱与被爱的一生。 佐野洋子用精美的插画故事讲述了一只猫从被爱到爱他人的故事。作者并没有开门见山地回答什么是爱,而是让我们跟随这只猫开始关于爱的冒险。这是一只活了100万次的猫,在猫过往的生命中,有着许多主人,国王为了荣耀,魔术师为了营生,水手为了解决船舱中的老鼠,饲养着猫。他们把猫当作工具,却也为猫流过眼泪,然而,在占有的姿态面前,猫似乎一点也开心不起来,哪怕人类为它流过再多的泪,也无济于事。“我已经不在乎死不死了。”可见爱不是傲慢给予,占有并不是爱。 在这只猫的第N次生命里,它获得了自由,学会了保护自己。获得自由的猫对爱充满了恐惧,似乎,爱别人便为自己戴上了枷锁。它不断重复着“我可死过100万次呢,我才不吃这套”。它拒绝了遇到的每一只猫,直到遇到它的白猫。面对白猫,它诚惶诚恐,它拥有很多爱,却不懂得如何再去爱,所以当它望向白猫,只是夸耀着自己的经历,换来一声“哦”。第二天、第三天……它并没有放弃,似乎,爱一个人可以卑微到尘埃,直到说出那句:“我可以跟你在一起吗?”阿兰·巴迪欧在《爱的多重奏》里说:“爱总是朝向他人的存在,他人带着他的全部存在,在我的生命中出现,我的生命于是就此暂时中断而重新开始。”爱将过往彻底清零,从今往后,我们也不再是那个自己。也正是从爱他人开始,爱似乎成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。 后来,白猫生了好多可爱的小猫,猫再也不夸耀自己的经历,它比喜欢自己还要喜欢白猫和小猫们。我们又何尝不是这只猫呢?爱一个人时,对方无疑成了我们生命的源泉。我们成家立业,做了父母,子女的幸福便大于了自己的幸福。似乎我愿意为了你,试着去爱世界,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生命和爱的体验。 可是呀,爱终有消失的一天。故事的结尾,白猫离开世界,猫抱着白猫,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。爱是痛苦的,但是,痛苦是否没有尽头?我们又是否应该开始?在故事的末尾,这位死了100万次的猫再也没有活过来。爱不但成全了猫,也成了生命的终点,爱留在了子女及恋人的记忆中。正如《寻梦环游记》中的精神世界,一个人的死去并不是终点,只要被爱的人铭记,他便不会消失。 《活了一百万次的猫》是普通人一生关于爱的冒险,它跨越时空,却也给人以力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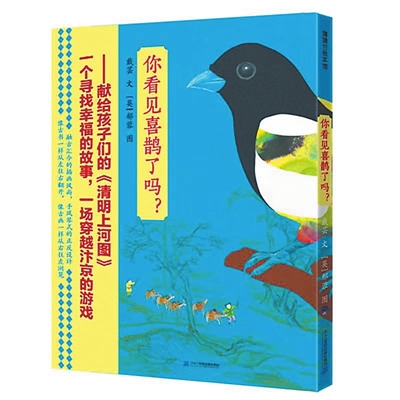
▲《你看见喜鹊了吗?》
戴芸/文 郁蓉/绘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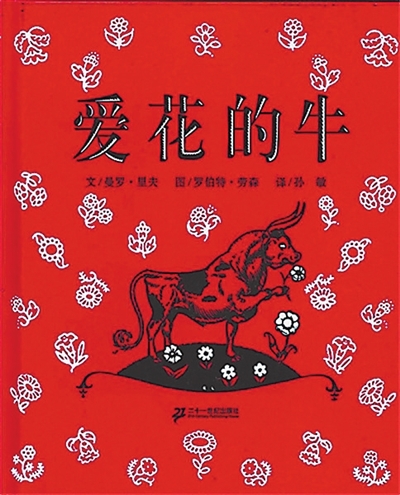
▲《爱花的牛》
曼罗·里夫/文
罗伯特·劳森/绘
孙敏/译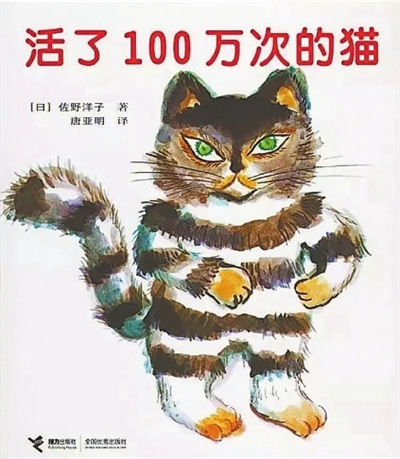
▲《活了100万次的猫》
【日】佐野洋子 著
唐亚明 译
接力出版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