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阅读】暮色里的泥土与诗心——读《雪峰山的黄昏》之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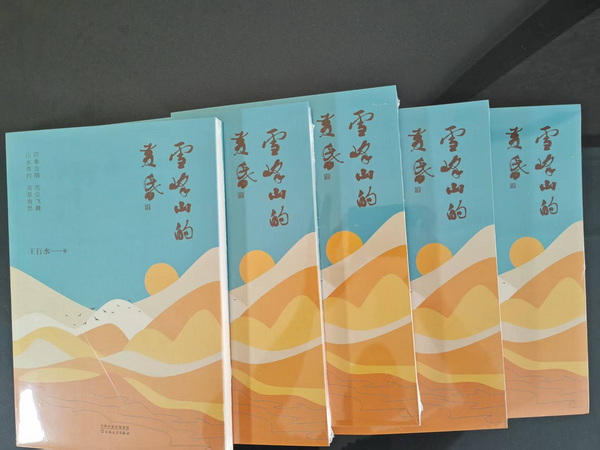
当《雪峰山的黄昏》一书在手中展开,仿佛有山间清冽的晚风,裹挟着松针、泥土和柴火灶的微息,拂过书页。这不是精致的案头清供,这是行水先生用脚板沾着暮色,在雪峰山的褶皱里,一垄一垄“耙梳”出来的日子。
读他的诗,眼前铺开的是雪峰山特有的黄昏画卷:不是遥不可及的霞光万丈,而是晒谷坪上渐渐收拢的金黄,还带着日头最后的暖意;是佝偻身影肩着柴禾,缓缓没入竹林小径的剪影,扁担吱呀的轻响仿佛就在山坳回荡;是木屋瓦楞间升起的炊烟,缠绕着腊肉和米粥的敦厚香气;是围炉夜话时爆出的爽朗笑声,像火星子溅在夜色里,烫得人心头一热。他的诗句里寻不见刻意的藻饰,字字句句都像刚从后山挖出的冬笋,裹着层层的壳,剥开来是山野的鲜脆与清甜,嚼一口,是这片土地最本真的滋味。
最令人心头发颤的,是那些在暮色浸润下,愈发清晰的坚韧与温情。一丛在夕照里摇曳的、最普通的芒草,在他笔下,成了“披着金光,向群山鞠躬的谦卑身影”,那在寒风中依然挺立的姿态,何尝不是这方水土养育的子民,面对生活的无声宣言?他写归巢的鸟,写灶膛的火,写溪流在暮色里低语的调子,写的都是雪峰山下,那些被黄昏温柔包裹的生灵与日子。他把对这片土地和乡亲们沉甸甸的眷恋,都细细研磨,融进了这些带着霜气和草木清芬的意象里。
读着读着,仿佛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:披着一身渐浓的暮色,裤脚沾着苍耳和露水打湿的草屑,刚从山径上走下来。他不再是灯下运筹的掌舵者,而是一个雪峰山的归人,一个暮色的歌者,用脚步丈量着光影的流转,用心灵谛听着山峦在黄昏里绵长的呼吸。那呼吸,是土地的吐纳,是村庄安眠的序曲,也是他胸腔里从未熄灭的、对这片土地滚烫的赤诚。
《雪峰山的黄昏》不吟唱虚幻的牧歌。它的力量,是岩石的沉默,是柴禾燃烧的噼啪,是霜打菜蔬的清苦,更是灶火映亮皱纹的暖意。行水先生以这本诗集低语:真正动人的诗篇,是浸透了霜色的晚云,是沉入大地怀抱的落日余晖。它生于斯,归于斯。读它,你的心会不由自主地沉静下来,随着那暮色四合时山野的脉搏,一同缓慢而有力地跳动。
合上书卷,雪峰山特有的草木清气与暮霭的微凉,似乎仍在鼻尖萦绕。行水先生的诗,像一捧带着体温的、雪峰山下的泥土,轻轻放在读者的掌心。它轻声提醒:最深沉的诗意,不在他处,就在这日日轮回的黄昏里,在生养我们的山川草木间,在父老乡亲被暮色镀亮的、平凡而坚韧的脸庞上。(艺之声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