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西吃辣排行榜!谁赞成?谁反对?
当菜市场门口卖早餐的阿婆从缸里取出今晨第一罐瓦罐汤时,赣江的晨雾还未散尽。麻糍包子糯米饭,小塑料袋装起打个结,赶早上班的人们匆匆拎上就走,像一阵烟似的,能踏踏实实坐在街边吃完一碗拌粉,谁说不算一种福气。
在江西,烟火气好像是守恒的。皮蛋肉饼汤的蒸汽接棒了江上的雾,窑里烧制瓷器的火舌也曾经轻舔过这片红色的土地。傩面在节庆的香火中忽明忽暗,朱砂飞扬,书院的檐角也早习惯了掩在青烟里,托起朱熹的月亮。
云横九派浮黄鹤,浪下三吴起白烟。陶令不知何处去,桃花源里可耕田?
这是一句反问,只要与这片土地耳鬓厮磨过一阵日月,自然就明白,这是被烟火沁润的江西,每个晨昏都生长着鲜活的故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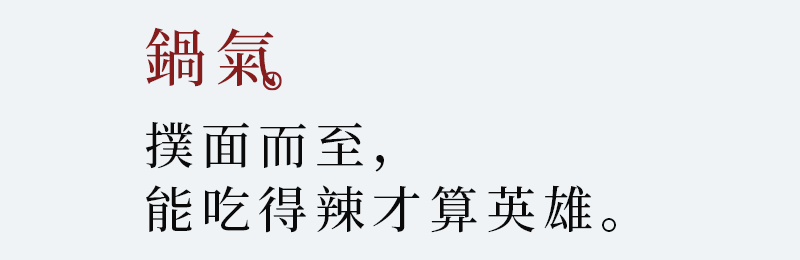
才进五月,走出南昌西就扑面一阵热浪,坐车一路向北,钻到市区最热闹的腹地,找一家小炒先解解馋虫。那店要门头旧旧,桌椅沉沉,食客攘攘,重要的是还没跨进门,已能感到一股热辣锅气扑面而至,才算地道。
江西的灶神定是位火爆脾气的红脸汉。当铁锅里的油开始冒烟,庖厨就不再是庖厨,而是战场:
腊肉片身先士卒,翻卷出金甲,青红椒碎激起第二波回合,火光倏地窜上,蒜末葱姜紧随其后,大勺在锅中滑动三圈,再锅边敲三敲,战鼓擂响,看烟熏的风味与香辛料在高温中过招,最后交出一把藜蒿,或一把蒜叶,总归是一抹绿色,像挥舞出凯旋的旗,撒盐,出锅——
你知道,那青花大碗的年纪可也不小,这辈子还没有盛过一次温吞无味的妥协。
当人们越来越愿意以美食作为切入点了解一座城市的时候,会发现江西如此丰富,当真是“物华天宝”,没来过的人大约已经听过“江西辣”的名号,来了之后才知道,即便是辣,也能辣出不一样的态度。
江西上饶紧邻浙江,吃东西也讲究一个“鲜”,恰好身边就守着一个鄱阳湖,新鲜水产丰富,鱼质鲜美,如此鲜与辣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。
鄱阳湖的另一边是九江,更是吃鱼大户,要知道鄱阳湖70%的水域都在九江境内,九江鱼块、黄豆鲩鱼、豆参烧鲶鱼、棍子鱼......在九江人手中,鲜和辣不是对手,它们是惺惺相惜的关系,烹制时加入辣椒的作用是把鲜味激荡得更悠长。
不过对于上饶和九江的辣,赣西人多少有点“不放在眼里”,说到底,还是“不够辣”。赣西的萍乡紧邻湖南,集湘赣食辣之大成,算得上是全江西最能吃辣的地方,“辣到哭”不是修辞,而是写实。这辣不绕弯子,不打诳语,只要出手,就是纯粹彻底,不留余地。
你或许有疑惑,单纯的辣有什么意思?非也非也。江西有道菜叫“辣椒炒辣椒”,其中青辣椒提供蔬菜的清新感,小米辣提供直白不犹豫的辣,糟辣椒提供发酵过的鲜,最后一把辣椒面,提供风干后的香。每一味辣椒都在拥有自身辣意的同时还能有所侧重,这可不是单纯的辣,这是辣的四次方。
小炒的盘底已经扫空,剩一汪红油,瓷碗里盘伏的粉正等待被嗦个干净,小锅里煨着的老鸭已经入味得很彻底。一顿饭,起承转合,在江西吃过,味蕾会有被惯坏的嫌疑,不然为何再吃别的,总觉得没有滋味?
已经不是过不过瘾的问题,谁叫灶火仿佛碰见辣椒就会更兴奋,谁叫人一看见那升腾的锅气就食欲大开?
怪不得江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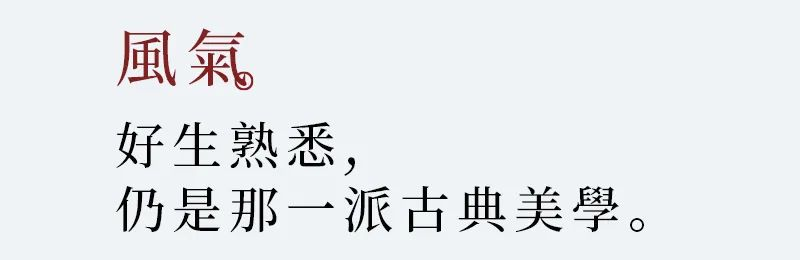
筷子撂下,抹抹嘴巴,青花盘子摞起被收走,还要再战十年。千年的窑火早已烧进市井的肌理,喊着下次再来的老板拖长音调,遥遥地听着,像赣剧老生一句浑然的戏腔。
江西的风味,味已经讲过,填饱了五脏庙,来感受这旧时风。
曾与江西好友共淋过一场雨,我们那时正在书店消磨时光,窗子上忽然溅了水滴,我们一同抬头看外面,她喃喃:落雨了。
我没听清她说什么,她用普通话平直的音调重复给我说,落,雨。
当“下雨”变成“落雨”,空气里的湿润忽然也带了点诗意。她说,江西十里不同音,各地方言里都留存了许多宋元时期的表达,平时跟家里人随口讲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,真写成文字才惊觉那种古典的美意。
比方把去年叫作“旧年”,年轻人叫作“后生”,午饭叫作“昼饭”,晚饭叫“夜饭”,回来叫“归来”,水开叫“水滚”,多少钱叫作“几多钱”,抽烟喝茶叫作“吃烟吃茶”。还有一个可爱的,是把小孩嘴馋,叫作“口水朵朵跌”。
江西的小孩,是在寻常对话的语调中,就在受宋朝美学的沁润的。
旧时的风会刮进博物馆里,作为时代的展品,但在江西,它不会将自己束之高阁,把世人遗忘,那些传统的民俗手艺,生活的调性,还依旧鲜活地存在着,继续下一代的依托。
江西有国家级非遗项目88项、省级项目560项,其丰富不必多说,感人的是那种随着岁月长河延续过来的“活着”的感觉。
瑶里古窑的龙窑依然保持着对火神的敬畏,当窑门洞开的刹那,天青色的月光便永远凝固在梅瓶之上;正月里的傩神庙前,带着面具的班主喊话,震得那周身的流苏乱颤;石城灯会可追溯至南唐,年年春节鱼龙舞,一个村庄的火光能映红整个星空。
还有还有兴国山歌、九江山歌、于都唢呐公婆吹,弋阳腔、青阳腔、萍乡春锣,更有歙砚、徽墨、文港毛笔……细数不尽也。
时代会更迭,但风气会因为与生活的相融,而长成一种态度。婺源三雕、南昌瓷板画、鄱阳漆器已然在以自己的方式阐释当代的东方美学,甲路纸伞、瑞昌竹编、夏布这些老手艺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成了新的潮流。
在赣南围屋的天井里,阿婆依照习惯以擂茶待客,那春日的新茶、饱满的芝麻花生在擂钵中星子般迸溅,恰似非遗艺术的基因在沸腾的生活中不断不断裂变生长。
无论何日君再来,仍是那绵柔的旧时风在贴面,仍是那一派古典美学做底子,这就是今日的江西。

眼下正是春光大好,朋友圈里已经有人凑好假,先出行大军一步抵达江西。我细问去哪儿,是奔着南昌登滕王阁,还是婺源看油菜花,还是山水都要,去九江一手庐山一手鄱阳湖?答曰:大差不差!最后腾出两天再去趟景德镇,为下半年离职放空踩踩点儿。
他不说我差点忘了。要是说几年前的年轻人离职也好gap year也罢,首选还是大理丽江,现在越来越流行去景德镇。问及缘由也很简单,这里本身拥有厚重的美学文化积淀,来了之后不怕无聊,不怕无事可做。陶瓷原本就是一种从生活到艺术再回到生活的美学,景德镇正适合收留那些漂泊太久不知如何生活吐息的灵魂。
如此看,江西当真是从不吝于提供给人前往的理由,无论是要吃要耍,要山要水,哪怕是今天打算做个田园梦,明天忽然想去乌托邦,只要你来,无有不应的。
江西的人气其实是天注定。要知道明清以前,这地方几乎没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争,反倒是每逢天下大乱,其他地区的民众会把这里当做迁徙地,这里自然灾害少,物产丰饶,宋元时江西人口一度占了全国人口10%-20%,手工业也随之发展,各种制造业兴盛不绝。
这样明媚奇瑰的地方,天生擅长养诗育墨。唐宋八大家中,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生于此地,还有黄庭坚、杨万里、晏殊、汤显祖……还有陶渊明,想想他是在这般山光水色里开创的田园诗派,顿觉一切都有迹可循。
魏晋以来,历代文人必经此地,光是咏庐山的诗,现在就留存有约一万六千多首。李白来这里望瀑布,苏轼来这里题西林壁,孟浩然隔着浩渺烟波在夜色之中停留,只为那一眼凝眸。这人气,其他名山追之不及。
江西亦有着悠久的办学系统,先后出现过大约一千座书院,岁月间摇晃的,不只树影,更是朗朗读书声。
文人墨客,理学大家,熙熙攘攘,回首发觉原来大家都来过这里。
这就是江西的人气。
暮色漫过景德镇的老窑址,新匠人正点着灯,将灵感付诸于陶土。白鹿洞书院被夜笼罩,晚风拂过屋檐,这风也曾吹散过朱子批注残留的墨香。当古老的吟哦在寂静的田野中再次响起,春天会从傩舞者的衣袖里抖落万千新绿。
你要不要回来,回来看看,这烟火里的江西。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