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村庄的深情
文/范泽木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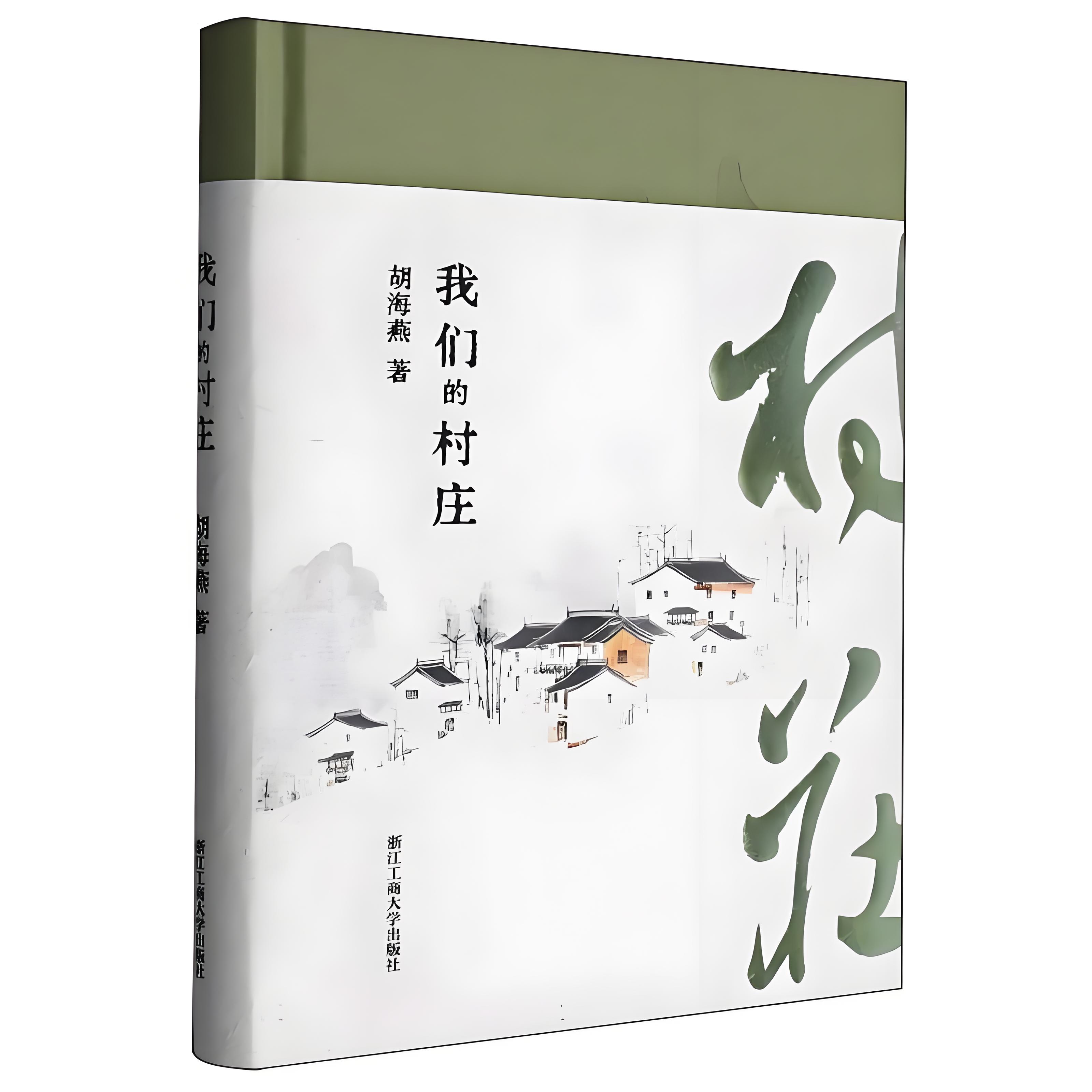
读胡海燕的《我们的村庄》,最令人难忘的是那满目葱茏的绿意。“绿色层次分明,深绿、浓绿、嫩绿、浅绿”,作者笔下的绿色不仅是视觉的感知,更是一种生命的浸润。“人走进去,绿了。苔藓走进去,绿了。缠绕的藤蔓走进去,绿了。”这种绿色仿佛具有神奇的感染力,即便是秋深冬初时节,也能感受到“春天正在醒来”的生机。这种对村庄色彩的敏感捕捉,折射出作者与乡村之间特殊的情感纽带。
与刘亮程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中冥想者的孤绝形象不同,本书的村庄呈现出一种温婉的气质,36个村庄或远或近,或亲或疏,作者总能以恰到好处的距离感与之相处。她不是村庄的旁观者,而是知己;不是过客,而是归人。在《去大皿看花》中,“有时随意走走,和朋友去后山那个叫‘虎爪岭’的地方择菜,下厨做一顿简单的晚饭,一个下午很慢又很快地过去了。”这样的文字,印证了王国维所说的“有我之境”——作者将自己的情感投射于村庄,又让村庄的景物承载这份情感,形成一种双向的滋养。
本书的写作还有着王国维所说的“不隔”境界。作者之所以能“不隔”地绘景抒情,在于她既捕捉村庄的外在形态,又深掘其内在神韵。写意与写实交融,虚与实如两根立柱,共同撑起本书的筋骨。在《神奇大盘山》中,她一反“群山之祖,诸水之源”的惯常表述,写道:“大盘山似乎是终点,让五千二百多座山峰聚拢过来,有序地排列起来,又似一个起点,让许多事物从这里出发。”这种独特的视角转换,既展现了景物特征,又融入了个人思考。在《遇见三水潭》中,她将新旧房子的关系比作“爷孙俩总能找着合适的方式,乐呵呵地处在一块”,从具象描写自然过渡到人情体悟,再升华至和而不同的哲理思考。这种由表及里、由实入虚的写作方式,让文字既有画面感,又有思想深度。作者写村口的大树:“它们是巧妙安排在村口的伏笔。绿意掩映下,村庄羞羞答答地打开自己。越往里头,越是敞亮。”树与村庄的从属、人文、审美关系,尽显于笔下。“不隔”正在于作者既能以画家的眼睛观察村庄形貌,又能以诗人的心灵触摸其魂魄,更以哲人的思辨体悟生命自然。
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《最忆是故乡》中对故乡尚路研村的描写。面对最该倾注感情的对象,作者却表现出惊人的克制。她努力地按捺住感情,以冷静的笔调描述留给她丰富记忆的故乡,以及如今的样貌变迁。这种“于浓情处克制,于寡淡处起波澜”的处理方式,反而让情感显得更加深沉内敛。在抒发对陪伴过自己的村口大树的感悟时,作者由物及人,道出了生命之间的永恒牵绊。这种克制而深情的表达,与艾青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的直抒胸臆形成有趣对照。
作者找到了观察乡村的新视角,她不是简单地怀旧或抒情,而是以村庄为媒介,展开对时间、生命、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。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,《我们的村庄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乡村、理解乡土的可能方式——不是将乡村视为过去的标本,而是作为持续生长的生命体,与我们的情感和思考紧密相连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