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书|与山河共情的灵魂之旅
文/子睿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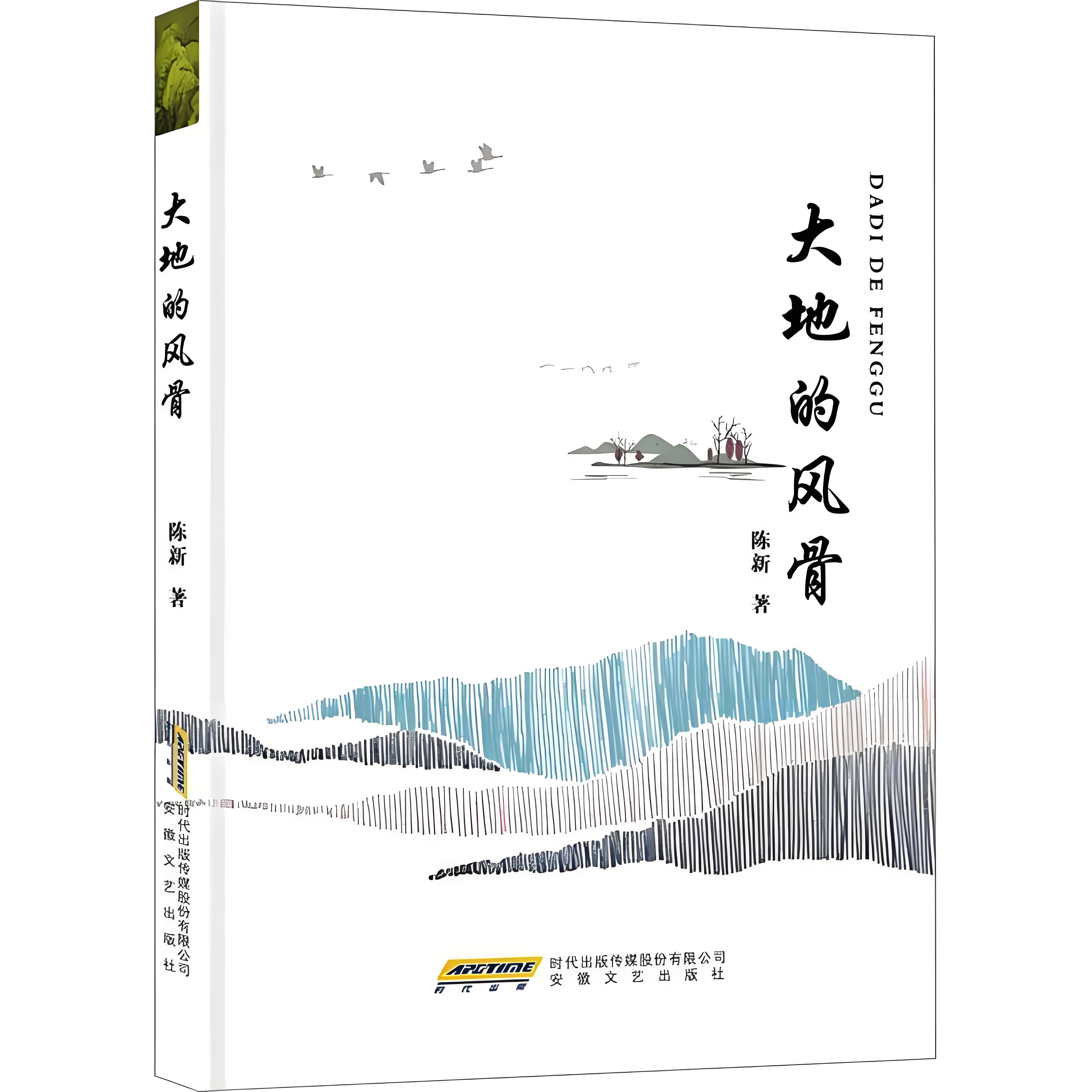
翻开作家陈新的散文集《大地的风骨》,仿佛推开一扇通向自然与历史深处的门扉。扉页间流淌的不仅是文字,更是一段以脚步丈量山河、以心灵叩问文明的旅程。作者以“行走”为笔,在天地经纬间书写的不只是风景,更是中国人血脉中绵延的风骨与不竭的乡愁。
书中,每一处风景既是历史的注解,又是时代的镜像。金石滩的嶙峋怪石,在作者笔下化作“大地的骨骼”,那些被海水冲刷的石头间,藏着千万年地壳运动的密码,也映照出人类文明与自然博弈的沧桑与不屈。当作者以哲人的视角及情感的触须凝视江河时,我恍然惊觉:原来时间的波光里浮沉着《诗经》的吟哦、战争的烽烟、文化的芬芳、精神的力量……
本书之风骨,既存在于大地之上,生于草木之间,又蕴藉于灵魂深处。“风骨”二字在书中被赋予了多重意象:它既是《清流如许》《远方的梦》的倔强,也是《凝华仙境的春天》《阆苑仙境》《九寨沟仙籁》的柔婉;既有《爱怨大通》《外婆的乐山》触及灵魂的爱,也有《大瓦山情歌》《花事桃源》《与荻港对饮》的优美环境。作者用“芭茅花”这一意象尤为动人——那些在秋风中摇曳的银色花穗,既是漂泊者命运的隐喻,又暗合着中国文人“野草韧如丝”的精神写照。
这种将自然景观、生态肌理、世相风物人格化的书写,让山河尘寰超越了地理意义的简单蕴涵,使之成为民族记忆基因传承及禅悟真谛的载体,让宏大的“风骨”概念变得可触可感。当读到一块普通的石头,作者说:“它不是山上一坨纯粹的被黑暗包裹或只见风雨彩虹的石头,它经历过白云苍狗的变迁,见证过祥和与屈辱,掠夺与屠杀,奋起和抗争,激越与沉寂。它是历史,是先辈,是修为旷达的逸士,是动静皆宜的尊者……”读至此处,仿佛脚下的土地突然有了温度与灵性,那些曾被我们匆匆略过的草木丘壑山川大地,原是如此深邃的文明现场。所谓文化传承,从来不只是博物馆里的标本,而是田间地头、市井烟火中生生不息的生命力。
在高铁飞驰而过的今天,作者的“行走”显得不合时宜却又弥足珍贵。他执拗地用双脚丈量土地,像古代文人那样实践“行万里路,读万卷书”。但这种行走绝非浪漫的逃离,而是对现代性焦虑的温柔抵抗——当都市人迷失在玻璃幕墙内,那些与古树对话、跟明月共饮、同山水唱和的时刻,恰恰提供了重新锚定生命坐标的契机。
书中令我眼眶湿润的段落很多,比如“明月峡记住或者见证的,又岂止渺如尘埃的儿女情长,和一腔澄澈如花的青春梦想?更有历史长河中令人唏嘘,令人惊艳,令人哀绝,令人扼腕层层叠叠的、一切一切由梦想编织的影像”;比如“在故乡,我时常深情地注视絮飞的芭茅花,它多像从故乡出去求学、打工的乡亲啊……慈祥与贫瘠无关,与爱有关。多少时候,我都想在光鲜的人丛中大喊一声母亲,你这位头插狗尾巴草只会生养红苕苞谷的故乡”……这些充满张力的文字与画面,恰是传统与现代和解的隐喻:文明的风骨不在固守或颠覆中,而在这静默共生的土地上。
值得一提的是,书的整体设计令人赏心悦目,素雅函套上水墨氤氲的远山,与内页烟霞流动的设计,使《大地的风骨》构成了一部“可触摸的散文”。当目光抚过那一行行意韵流连的文字,仿佛触摸到了宣纸的墨痕、青瓷的开片、碑刻的沧桑。这种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核的高度统一,提升了阅读的美学体验。
合上书页,窗外的车流依然喧嚣,人潮依然忙碌,但心底已悄然筑起一座静谧的山水庭院。作者以草木为镜、以山河为尺,勾勒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轨迹,将个体感知与民族记忆相融合,唤醒了我们基因里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密码。或许这正是本书的力量——它不提供我们一直在找寻的答案,却种下了一颗种子,让我们在与一束芭茅花,与一坨石头,与一棵古树,与一片树叶,与一条栈道,与一朵花儿,与一幢旧宅……相遇的某个时候,突然读懂了大地的语言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