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书·抗战丨纸间烽火:战时知识分子的无声之战
文/子 安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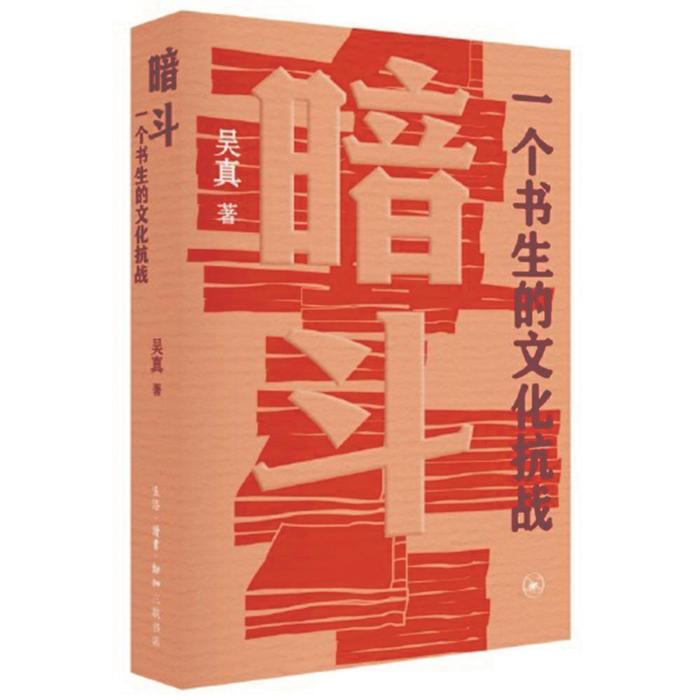
1938年秋,上海。炮声暂歇,寒气透骨。听闻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现于书肆,郑振铎在家中踱步良久,抓起磨毛边的旧呢外套出了门。脚踩在弹坑累累的街面,心悬着古籍随时湮灭的焦灼。吴真《暗斗: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所写的,不是孤胆英雄的传奇,而是一群沦陷于泥淖,以纸为甲、以智为盾,默守文脉星火的读书人。他们的战场,在那些脆黄的书页间。
租界已成“孤岛”,留下者各有千斤重担。郑振铎无法西行,家中老母在堂,幼子待哺。那句“走不得”,是一群心照不宣的同道之音。1940年初春,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于危城悄然结成。郑振铎、张元济、张寿镛、何炳松诸先生,借“星六会”小聚之名碰头。茶盏轻响间,消息暗递、款项交割,眼中的忧色化不开。开明书店的店员成了暗流舟楫——他们屏息将善本夹入识字课本,冒险运往香港,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在那头接应,暂护流徙的文脉。当敌伪暗哨盯得郑振铎寸步难行,是来薰阁老板陈济川豁出身家,将珍本拆散混入废纸捆,才送出险境。
1940至1941年,无声之战陷入深涡。日本“东方文化学院”披学术外衣,行劫掠之实。服部宇之吉、长泽规矩也等深谙汉籍,其学识竟成劫掠罗盘。战前,长泽规矩也与郑振铎书信往来,互借珍本,尚存学人温煦;战时却参与对华文化“调查”,实为掠夺前哨。1941年冬,香港陷落,同志会暂存于此的三万册珍籍,尽落敌手,掠往东京。那一刻,书生们心如坠井。
在沦陷区喘息,步步如履薄冰。郑振铎背负如山。大后方挚友叶圣陶的信,字字恳挚如烙:“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,战地之伤残破坏,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……”此乃对苍生劫难的剜心之痛,亦是对故人之路的深叩。作者细梳中日档案、汇款存根、洇墨日记,捞出众多无法抹去的身影:曾解囊的张叔平,身份若雾中行舟,游弋各方势力间;学人陈乃乾将《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》重现之讯首发于日本《书志学》杂志,既有欣喜之切,或亦含惑敌之机;王统照、李健吾等作家于“言”与“默”的夹缝中辗转,以切实行动代呐喊之声。一本本寻回藏匿的古籍,便是文明薪火的无声传递。
烽火连天中,泛黄书页所载,早越疆界硝烟。郑振铎视抢救如搏命:“为国家保存文化,如在战场上作战。”其目光不独尊宋元古椠,亦重方志、舆图、宝卷、俚曲,它们是文明深扎的老根。闻香港三万册书终落敌手,郑振铎信中书:“中夜起坐,泫然不能自已……一朝毁弃,万金莫赎。”这份文化悲悯与担待,刻进了那代人的骨血里。而郑振铎详录的“香港装箱目录”,这本不起眼的簿子,顿显千钧之力——它成战后追索国宝的凭据,漂泊的国宝终于归家。学问的根柢,于乱世成了钉住文明的锚。
本书的回响,系于三万册书的漂泊:从枪炮呼啸的上海滩,至暂歇的香港岛,再陷敌手的东京湾,终安眠北京书库。摩挲历经劫波的纸页,似仍触到旧年尘灰、海港咸腥、异乡寒霜,让人看到了那代读书人在至暗长夜死攥文脉的犟劲,他们弓腰护住的,岂止几张薄纸?当是文明寒冬中依然搏动的脉息。
当整个民族于黢黑的历史甬道中摸壁前行,这群书生以手为杖,以心火为灯,在文明的断垣残壁间,一寸寸抠出那条通往熹微的窄径。书页翻动的窸窣声,便是那死寂年月里,最铿锵的心跳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