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书|鹿铃悠悠
文/程嘉怡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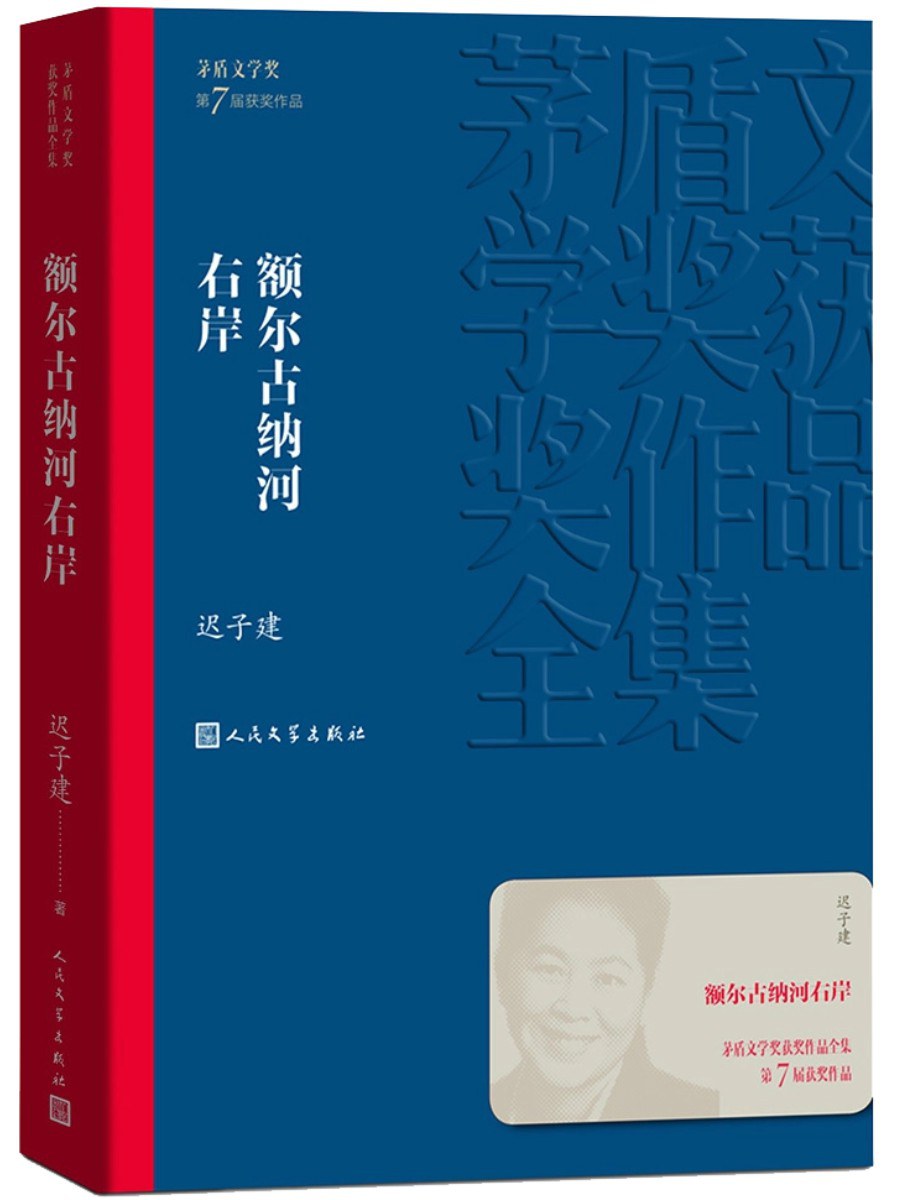
“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,我有九十岁了,雨雪看老了我,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”。
迟子建的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像一条蜿蜒近百年的河流,而它的源头是大兴安岭中一场已近暮年的雨,这场雨落在了一个仅剩两人的部落,落在了形单影只的希楞柱,也落在了一个鄂温克族老妇人渐渐浑浊的眼睛里。这无名的老人对着延续了三代的火种讲起一段往事,呢喃的话语中带着驯鹿的铃声、萨满的吟唱与森林的回响,这是一个游牧民族的百年史诗。
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鄂温克族崇尚驯鹿,在他们看来,驯鹿的眼睛是白天的太阳、夜晚的星辰,而每次搬迁时的悠悠鹿铃所指引的方向,就是民族灵魂的归处。
这个与驯鹿为伴、与森林共生的质朴民族,有着跌宕起伏的命运。书中说,人们出生是大同小异的,死亡却是各有各的走法,从列娜骑驯鹿坠入雪地冻死,林克被雷击身亡,到瓦罗加死于黑熊之手,死亡气息笼罩着这个部落。但正是在这样的叙事中,生命的坚韧才更加动人——鄂温克人并未沉沦,而是以近乎诗意的姿态与自然对话,在严寒中点燃篝火,在风暴中守护驯鹿,在失去中学会告别。生命如同大兴安岭的白桦林,看似脆弱,却能在冰封中积蓄力量,在春天破土而出。书中的鄂温克人遇到过信念与世俗的冲突,也亲历过现代化浪潮对游牧文明的侵蚀,但林间松涛下的悠悠鹿铃从未与他们分离。他们是森林的儿女,额尔古纳河赋予他们生命,甘甜的白桦树汁滋养他们,而温良的驯鹿陪伴他们。
本书最动人的部分,或许就在于它对自然的礼赞。迟子建笔下的大兴安岭是一个充满灵性的世界。鄂温克人狩猎前会向山神祈祷,用熊骨听风吟,披鹿皮看星河,将生死融入自然循环。这些仪式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诗意。而迟子建的描写更是将这种诗意推向极致:“我这一生能健康地活到九十岁,证明我没有选错医生,我的医生就是清风流水,日月星辰。”
正是在驯鹿、树木、河流、月亮和清风的孕育下,这片土地上的鄂温克人信奉玛鲁神,这位脱胎于森林的神明穿着犴皮制成的衣服,喜欢听鹿皮小鼓的敲击声。在书中,萨满的神秘色彩与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交织,赋予小说一种超越时空的气质。妮浩作为萨满,她的每一次仪式都是一场与玛鲁神的对话,也是对生命本质的叩问。这些描写仿佛从土地中生长出来,带着雪原的冷冽与森林的温润,让人在阅读时感受到震撼。
然而,本书并非只是一部田园牧歌式的史诗,它也是一面镜子,映照出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明经历的阵痛。鄂温克人从森林走向城市,驯鹿被栅栏囚禁,希楞柱被钢筋水泥吞噬……伊莲娜从山林走向城市,却始终无法摆脱精神的漂泊,最终留下带自己走出大山的画笔,只身投入故乡的河水;安草儿坚守着最后的驯鹿群,却只能在空寂的山林中与风声对话,等待不知何时才会回来的那只纯白驯鹿。迟子建以温柔而克制的笔触,展现了人类在追求技术进步与守护精神家园之间的两难。当人们走出森林,物质生活或许得到了改善,但灵魂却仿佛被抛入了无根的漂泊。这种“失根”的焦虑,贯穿全书。
本书留给我们的,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记忆。当最后一位酋长的妻子的身影在火种中渐渐模糊,额尔古纳河的流水却依然奔涌不息。这部作品如同一次深情的文化回望,让我们在浮躁的当下,重新审视文明的价值,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。在书页翻动的间隙,我们仿佛能听见驯鹿的铜铃在风中轻响,额尔古纳河亲吻着森林,这是一个民族对土地的深情告白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