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书|流浪中的精神安顿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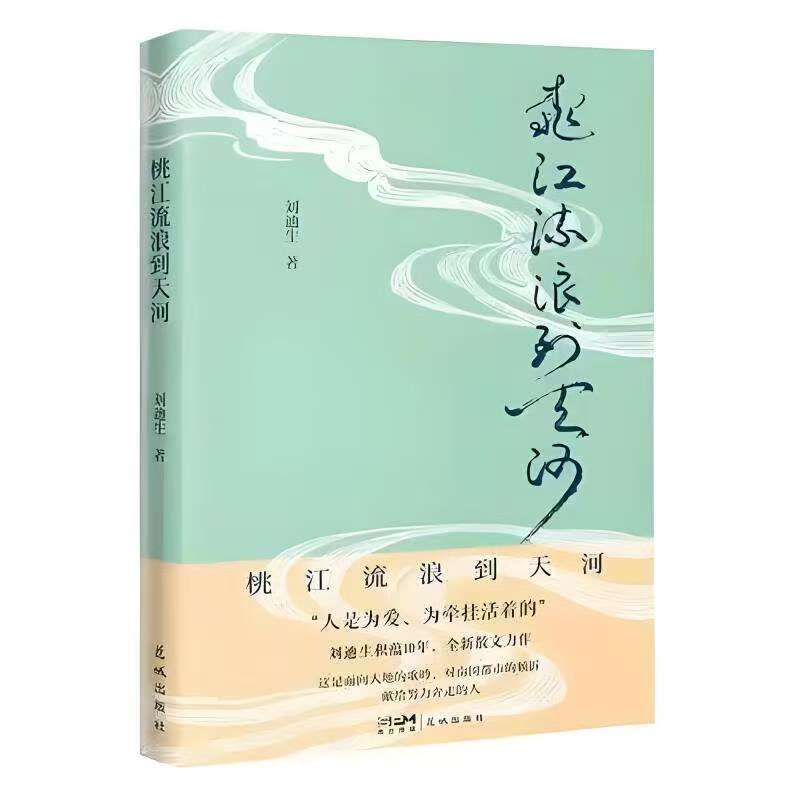
▲《桃江流浪到天河》,刘迪生著,花城出版社。
散文集《桃江流浪到天河》以“地理迁徙”为显性线索,以“精神扎根”为隐性内核,在故乡与异乡、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,编织出一幅充满生命温度的散文长卷。从江西信丰的桃江到广州天河的都市,不仅是空间的跨越,更是一个文人在时代浪潮中对“家园”的重新定义——故乡不再是固定的坐标,而是流动的情感;异乡也并非漂泊的驿站,终成精神的归宿。
地理叙事中的生命轨迹
《桃江流浪到天河》这个书名充满文学张力与想象空间,仿佛一条跨越千里的精神脐带,一头系着乡土的根脉,一头连着都市的脉搏。
“桃江”作为具体的地理符号,不仅是江西信丰的“母亲河”,更是作者记忆里鲜活的生命场域。他笔下的故土风物带着农耕文明的温润厚重:“三月,橙树花开,洁白如雪”;“立冬,脐橙果大色艳”(《信风吹来一枝春》)。春秋更迭间,既见物产富饶,更藏着对土地的深情——那“巧笑倩兮”的脐橙,是舌尖甘甜,更是心头乡愁。文章融入信丰的历史文化,让乡土记忆有了纵深。大圣寺塔的苍迈、桃江八景的灵秀、玉带桥的雄浑,在砖石间凝固千年文脉;古迹楹联更显文化传承的自觉。桃江的“流浪”,是少年背上行囊时,回头望见的那抹波光;是异乡街头闻到橙香时,心头泛起的涟漪;是作者笔下反复描摹的故土影像,成为乡愁里永不褪色的底色。
而“天河”作为广州核心城区,是现代都市文明的浓缩象征,与桃江形成鲜明对照。“滔滔天河浪,滚滚珠江潮”(《璀璨的天河》),这里的“浪”与“潮”早已挣脱自然律动,化作都市脉搏的奔涌——体育西路地铁站“每天数十万人头攒动”,是工薪族步履匆匆的剪影;天河花市“繁花环绕如燃烧的花城”,是市井烟火的热烈绽放;如“高大挺拔的亚热带植物”的天河体育中心,是城市发展雄心的具象(《璀璨的天河》)。作者虽曾“寄身其中,随波逐流”,却在体育中心的晨跑中踩准城市节奏,在花城广场的灯火里触摸到归属感。天河的“接纳”,完成了异乡到故乡的蜕变,更昭示着现代文明中精神扎根的可能。
从桃江到天河,两个意象的碰撞,恰似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对话,乡愁与机遇的交织,最终在“流浪”的轨迹里,写就一个人对“家园”的重新定义。作者的迁徙过程绝非简单的地理位移,而是一段布满生命温度的“扎根—迁徙—再扎根”的成长史诗,每一步都印刻着时代浪潮与个体命运的交织。
在从化的十年,是他生命中“向下扎根”的关键阶段。这片被北回归线温柔拥抱的土地,不仅见证了他职业身份的多元蜕变——“做过美工、秘书、导游、婚纱摄影师,甚至亚运会摄影记者、建筑助理工程师”(《我深爱的这片土地》),更承载着他从青涩到成熟的精神蜕变。流溪河是他的“心灵镜子”,“温柔恬静的吟唱”映照着他初入社会的懵懂与憧憬;温泉是他的“生命熔炉”,“再也按捺不住的激情”淬炼出他面对生活的韧性与热忱。他曾在荔枝节加班到凌晨两点,拿着不足400元的报酬时迷茫过;却也在流溪河森林公园的山顶,被“晶莹剔透的水、郁郁葱葱的树”击中,瞬间爱上这片“北回归线上的绿洲”(《我深爱的这片土地》)。在这里,他“贪婪地汲取着色彩斑斓的岭南文化”,让异乡的水土真正融入血脉,成为无可替代的“第二故乡”。
扎根天河的岁月,则是他“向上生长”的绽放期。从体育中心东门的晨跑轨迹里,能读出他与城市的默契——“耳边响着曼妙的音乐,一边小跑一边想着心事,偶尔会有一些关于写作和工作的灵感涌现”,他的几部作品就在这日复一日的脚步中悄然酝酿(《璀璨的天河》)。花城广场的喧嚣不是干扰,而是归属感的注脚:“与家人、朋友三三两两在花木中间穿梭”,他在骑楼的斑驳光影里看见历史,在霓虹灯的璀璨闪烁中触摸当下。当他说“天河,我真的爱上了您”,这句直白的告白里,藏着从“异乡客”到“广州人”的身份转换,更藏着对“日久他乡是故乡”的深刻体认。
从信丰到从化再到天河,这三段地理坐标串联起的,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命路径,更是改革开放后千万城乡迁徙者的共同缩影——他们带着故土的印记,在异乡的土壤里艰难扎根,最终让流动的岁月沉淀为生命的厚度,让“流浪”的履痕生长出“家园”的模样。
人情书写中的大爱底色
陈剑晖教授在序言中精准点出:“爱是刘迪生这本散文集的底色和基调。”这种爱绝非浮泛的抒情,而是如流溪河的清泉般,渗透在字里行间,在亲人的深挚爱里、友人的笑谈中、故土人的烟火气里,流淌出“人道与天道和谐共处”的温润境界——既有对个体命运的深切凝视,也有对天地万物的悲悯情怀。
对亲人的爱,藏在最朴素的细节里。写父亲时,字缝里藏着深沉的理解:父亲作为乡村教师,在“读书无用论”盛行的年代,坚持给学生补课,甚至从微薄工资里为贫困生垫付学费,“至今仍未收回分文”。这种“严”与“慈”的交织,恰是中国式父爱的真实模样——如桃江的流水,看似冰冷,实则滋养万物。写母亲时,他笔锋柔软:“小时候总盼望下雨,因为只有下雨天,母亲才不出去干活,在家缝缝补补”(《母亲的河声》)。寥寥数语,道尽客家女性“用刚强和隐忍撑起一个家”的坚韧,让母爱如流溪河般,温柔却有力量。
对友人的爱,则带着江湖气与知己情。记好友鲍十,他写两人在天河北喝酒的常态:“鲍十最喜欢微醺的感觉,享受那种放松,享受那种无我的状态。他总是一边喝酒,一边乐呵呵地小笑,喝到兴奋时,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”(《酒友鲍十》)。没有豪言壮语,却写出文人相交的默契——如同天河的灯火,彼此照亮,互不打扰。写雕塑家洪波,他聚焦其工作室的细节:“三面墙壁立着书架,上面挤满雕塑模型,人和神、远古和现代、东方与西方都浓缩在这里,风拂来,满室天香”(《捏弄心灵》)。字里行间不仅是对艺术的欣赏,更有对友人“借钱给朋友,自己连续七天靠矿泉水充饥”的仗义的敬佩,让友情在岁月里沉淀出温润的光泽。
而对故土之人与天地万物的爱,更显博大。他写从化的乡民,记下他们谈论“陈书记为我们修村道”时的自豪(《总想把句号画得圆一点的人》);写信丰的农人,描摹“雷惊菜花,雨推稻浪”里的辛劳与期盼(《为信丰记》)。即便是草木山石,在他笔下也有了灵性:“从化的每一滴水珠都珍藏着故事,每一片树叶都谱写着旋律”(《我深爱的这片土地》)。这种爱,从对“人”的关怀,延伸到对“万物”的敬畏,恰如陈剑晖所言,是“天地万物皆有情的大爱”,让散文集在私人叙事中,照见了时代的温度与人性的光辉。
更动人的是字里行间对普通人的深切悲悯,如暗河潜流,在具体而微的生命沟壑里静静流淌。写《香云纱》时,他没有止步于非遗技艺的精妙描摹——“用广东特有的植物薯莨汁水多次浸泡,经特殊工艺加工而成”,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与丝绸共生的工匠:“要一次又一次浸泡莨水,一遍又一遍过河泥”,更特写“摊雾工序”的细节——“夕阳落下后,将坯绸平铺在草地等候雾露,坯绸吸水后慢慢变得飘逸柔软”(《香云纱》)。那些在晨光暮色中翻动面料的手掌,那些被薯莨染成褐色的指尖,让这匹“软黄金”不再是冰冷的奢侈品,而是承载着劳动者体温与呼吸的生命载体,每一寸光泽里都藏着“天地雨露出神采”的辛劳。
这种爱从不局限于血缘与熟稔,而是如珠江潮水般漫过个体边界:写从化村道上赶车的农民,记下他们说“陈书记为我们做了大好事”时的淳朴笑容(《总想把句号画得圆一点的人》);写荔浦抗战老兵,还原他们“拒绝日军300万银圆行贿”的铮铮骨气(《山河的痉痛》)。从具体的人到群体的命运,从私人的感动到对生命共同体的关怀,这份悲悯让散文有了超越个人叙事的温度,如北回归线上的阳光,平等地洒在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身上。
文化观照中的守正创新
作为岭南文化的亲历者与书写者,刘迪生的散文始终带着对地域文化的自觉观照,如同一位细心的文化匠人,既小心翼翼守护着传统的根脉,又从容拥抱时代的新机,在古今交织中编织出岭南文化的鲜活图谱。
他对传统的坚守,藏在对历史遗存的深情凝视里。写广州北京路时,他不满足于描摹商业繁华,而是穿透水泥路面,发掘“唐、南汉、宋元、明清、民国11层路面遗迹”,在“双门底”的市井烟火中,读懂铜壶滴漏“准点报时”的智慧,让“千年商都”的基因在骑楼的斑驳光影里缓缓流淌(《永远的女神》)。记客家山歌,他不仅记录“哎呀嘞——哎”的独特腔调,更捕捉“过山溜”里的生命密码——“源于龙南扬村乡,山民为邀同伴、惊散猛兽而唱”,让这穿越山谷的歌声,成为客家人“迁徙中坚韧品性”的活态见证(《客家山歌入梦来》)。即便是文言写就的《为信丰记》,也绝非炫技式的仿古,而是用“玉带桥前清故物,巨石叠垒”的笔墨,让故乡的历史脉络在对仗工整的韵致中愈发清晰。
对时代新机的拥抱,则体现在对文化传承的现代思考中。写从都庄园,他既惊叹“唐代仕女雕塑与国际峰会的碰撞”,也点赞“高尔夫球场与古村落的和谐共生”,让传统园林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的生命力(《北回归线上的一墨醒笔》)。记天河体育中心,他看见“六运会的呐喊与亚运会的欢呼”在此交织,更发现“恒大球迷称其为‘天体’”的当代共鸣,让体育场馆成为城市精神的新图腾(《璀璨的天河》)。就连非遗技艺香云纱,他也不局限于“薯莨染色、河泥晾晒”的古法,更关注“现代设计师融入时尚元素”的创新,让这匹“软黄金”在国礼舞台上绽放新的光彩(《香云纱》)。
这种“守正”与“创新”的平衡,恰是岭南文化“海纳百川、敢为人先”精神的写照。正如他在《啊,南风》中所言:“广东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百舸争流,是海洋与内陆文化碰撞的咸淡水高地”,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,刘迪生不仅记录着文化的变迁,更成为文化传承的积极参与者——用笔墨为岭南文化注入新的时代注脚。
在艺术表达上,作者同样展现出“守正”与“创新”的圆融共生,如同一位娴熟的民乐演奏家,既能奏出古曲的悠远韵味,也能融入现代旋律的明快节奏。写《为信丰记》时,他毅然选择文言这一古老载体,笔下的故乡风物在凝练的字句中焕发出历史的厚重感。“玉带桥前清故物,巨石叠垒,高古雄峙”,寥寥十二字,既以对仗工整的句式重现古桥的苍劲姿态,又以“高古雄峙”的气韵勾勒出岁月沉淀的沧桑;“大圣寺塔直凌霄汉,九层六角,九层九境界,六角六画图”,则以排比铺陈的笔法,将古塔的形制与意境层层展开,让文字自带建筑般的立体感(《为信丰记》)。这种对古典文脉的接续,并非刻意仿古的炫技,而是因故乡的历史纵深与文言的古朴气质天然契合,仿佛唯有这般凝练的语汇,才能承载“信丰者,幽居赣南,弹丸于泱泱华夏”的绵长记忆。
而书写《指数星辰》中鲁迅文学院的经历时,他又切换为舒展的现代白话,让情感在直白的表达中自由流淌。“鲁院的风,鲁院的雨,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历史文化长河的波峰浪谷,千回百转”,以“风”“雨”为喻,将鲁院的精神传承具象化。这种白话的鲜活与灵动,恰如其分地传递出当代文人面对精神洗礼时的赤诚与激荡。
从文言的典雅蕴藉到白话的率真直白,作者在语言形式的切换中,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:让传统文脉在现代语境中苏醒,让当代精神从历史土壤中汲取养分。正如他笔下的香云纱,既保留“薯莨染色、河泥晾晒”的古法,又融入现代设计的巧思,最终在文字的经纬中,织就一幅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艺术锦缎。
从桃江到天河,刘迪生书写的不仅是个人的迁徙史,更是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。在“流浪”的表象下,是对“家园”的永恒追寻——这种追寻不再依赖地理的固定,而在于内心的丰盈。正如风“在路上,故乡就在路上”,作者最终在文字中安顿了漂泊的灵魂,在爱与被爱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家园。
文/马忠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