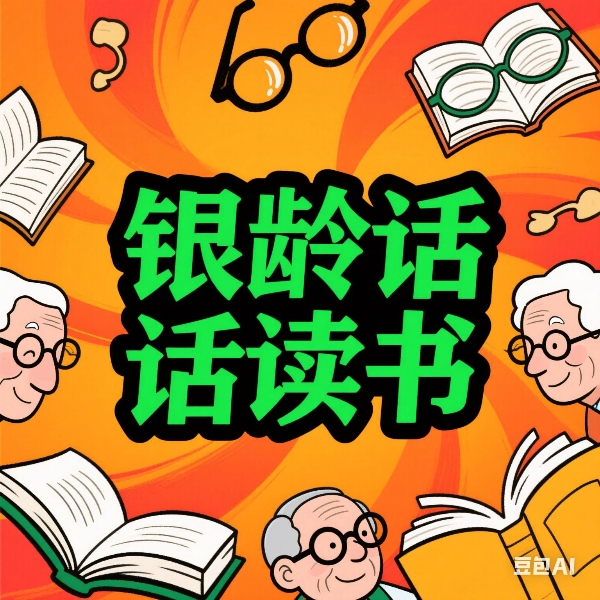【银龄话读书】(十)读书,要如胶似漆

宋一叶
“如胶似漆”一词,最早见于《史记·鲁仲连邹阳列传》:“感于心,合于行,亲于胶漆,昆弟不能离。”原指人与人之间情谊深厚,如同胶漆般难以分离。而读书之道,亦应如此。胶与漆相遇,彼此交融,难舍难分,恰似读书人与书籍相逢时迸发的极致眷恋。唯有如胶似漆般地投入,方能与书相融,沉浸其中,与书神交,与智者为友。
穿越时空,回望岁月,在卷帙浩繁的典籍中,有无数如胶似漆读书的动人故事。东汉学者王充虽然家贫无书,但他把读书视为生命的感官延伸。他常常站在洛阳书肆地摊上看书,双目紧盯竹简,手指无意识摩挲书页,哪怕腹中饥饿、双腿酸胀,也舍不得挪开半步,如胶似漆般痴迷沉浸其中;宋代文豪陆游,八十年间“万卷虽多当具眼”,哪怕年迈体衰,仍坚持“读书夜达晨”。他在《冬夜读书示子聿》中写下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”,字里行间流淌着对书籍如胶似漆般的深情眷恋……
近代文人更是以血肉之躯演绎读书的胶着深情。翻译家朱生豪在战火硝烟、贫病交加的窘境中,蜷缩在昏暗阁楼里,仍然用冻僵的手指在稿纸上翻译着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书页间满是他咳嗽时溅落的血渍;作家萧红在颠沛流离的动荡岁月里,把书籍视同精神铠甲,始终将《生死场》《鲁拜集》的手稿贴身收藏,恰似胶漆相粘,不离不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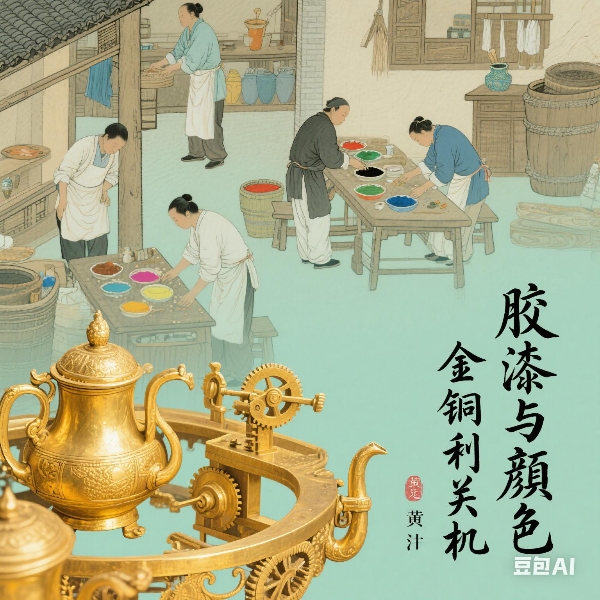
如胶似漆地读书,是书人合一、物我两忘的沉浸体验。孔子读《周易》“韦编三绝”,因反复翻阅而使竹简的牛皮绳断裂;董仲舒“目不窥园”,三年不观庭院花草;李密“牛角挂书”,骑牛访学仍手不释卷,如此等等,都是入书化境、如胶似漆的极度专注。
如胶似漆地读书,是情感契合、情智交融的精神交流。黄庭坚诗云:“胶漆与颜色,金铜利关机”,喻指读书时思想与文字的紧密交融。林纾家贫,在墙上画棺材并题“读书则生,不则入棺”,视书如命;顾炎武每年温习旧书,“边默诵,边请人朗读”,在反复咀嚼中体悟真知。正如培根所言:“读书使人充实,讨论使人机智,笔记使人准确。”当读者与作者思想契合,或击节称叹,或掩卷长思,如此这般精神的交融,远胜浮光掠影的泛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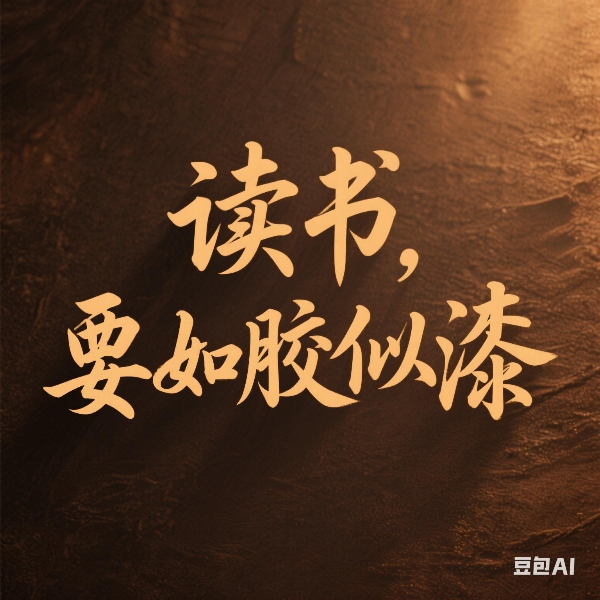
如胶似漆地读书,是知行合一、融入生命的践行转化。如爱因斯坦所言:“教育就是当一个人把在学校所学全部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。”陆游诗云:“附著以胶漆,入用更可怜”,强调知识需与实践结合。王阳明提出“知行合一”,认为“知而不行,只是未知”。现代教育也强调,真正的读书人,都该有“如胶似漆”的执着,让书页与掌心相贴,让文字与心跳共振,让知识与生命永远缠绕,并能将其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
或许,真正的读书人如胶似漆地读书,是人与知识相依相拥、共生共存的生动写照。古人云:“读书须用意,一字值千金。”当我们翻开一本书,便开启了一场漫长的心灵交融:读哲学,是与苏格拉底的思想胶着辩论;读历史,是与司马迁的笔触紧密纠缠;读文学,是与曹雪芹的灵魂共筑梦境。如此文字与心灵紧密相贴,书籍与生命深度相拥,读书便不再是简单的信息摄取,而是一场知识与灵魂的胶着共生,一次跨越时空的永恒相拥。
如同胶漆渗透每一寸纤维,在当今数字化、信息碎片化的今天,如胶似漆的读书精神愈发珍贵。唯有如胶似漆地读书,方能在喧嚣中守住本心,在浮躁中沉淀智慧;唯有如胶似漆地读书,才能让文字融入血脉、思想重塑灵魂,从而抵达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的境界……